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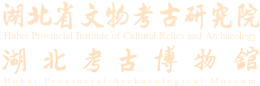
在九里岗考古工地,随着探方内的土层被层层拨开,一座座“陶山”在折叠桌上堆积起来。这些灰陶、红陶的残片,如同被时间揉皱的密码纸,闪烁着六千年前的微光。这是九里岗考古队工作日常的一部分,而他们的重心,此刻正转入室内整理阶段——陶片整理。
面对这些残破的陶片,考古队员们的工作并非简单地堆砌或丢弃。他们双手轻捧起一片片陶片,仔细观察陶胎中的蚌壳颗粒,这是大溪先民制陶时为了防止开裂而掺入的“配方”,就像是陶器的DNA。队员们按照质地、颜色、纹饰进行细致的分拣,每一片陶片都被赋予了它应有的位置。

然而,陶片整理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更是考古类型学精妙之处的展现。公众往往惊叹于博物馆里完整的陶罐,却不知它们诞生于千万碎片的逻辑重组。

考古类型学,正是这样一门科学便捷的方法论,它帮助考古学家系统地分析研究这些庞杂的遗存。
考古类型学,简单来说,就是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排比,以揭示遗存特征及其演变的方法。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分类,将遗物按不同质地分为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铁器等。陶器再根据器形用途分为釜、鬲、罐、瓮、缸、盆、钵等。这样的分类过程,就像是在划分动物的纲目科属种,使得庞大的遗存资料变得条理清晰。

但分类只是开始。归属于同一器类的器物,往往差别很大。这就需要结合遗物出土的地层顺序来观察、排比、归纳器物的共存关系及演化规律。考古队员们通过地层关系,对陶罐等器物进行更为细致的型式划分,用“型”代表每一个器类下存在的小类亚类,用“式”代表每一小类亚类的演化顺序。这样的划分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必须经过所有地层关系的检验。
类型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对遗物进行分类和型式划分。更重要的是,它要在认识遗存特征和变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横向上,具有稳定共存关系的器物可以视为同时代的遗存;纵向上,各型式的器物演变排序则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这就像是给散乱的书页恢复章节目录页码,并按照图书分类目录放到合适的书架位置上。
在九里岗考古队的陶片整理工作中,考古类型学得到了生动的展现。队员们通过仔细分拣和观察陶片,不仅揭示了陶器的制作技术、纹饰风格等特征,还通过地层关系和型式划分,构建了这一地区陶器演变的时空框架。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准确地判断陶器的年代、文化属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
陶器作为日常使用最广泛且容易破碎的器类,其器形变化速度比较快。因此,依据多变的陶器器形变化,考古学家可以获得更为精确的时间表。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特别青睐陶器的原因之一。

当晨光再次漫过探方,那些曾被视作“破瓦烂罐”的陶片,已在考古报告中化作文明年轮。从手制到轮制、从圜底到圈足、从实用器到礼器……陶器形态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先民在时间长河中刻下的航标。而考古类型学,就像是照亮这些碎片棱角的灯塔,让消散在历史虚空中的陶轮转动声、陶窑爆裂声、孩童打水时陶罐与井壁的碰撞声,在现代人的耳畔重新苏醒。通过陶片整理,我们不仅看到了陶器的演变历程,更看到了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