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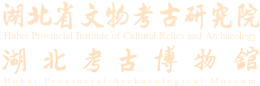
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楚考古发现与研究
对楚文化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从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开始的,此次共发掘160余座墓葬,其中战国楚墓73座[1]。湖南省博物馆又在长沙先后发掘了千余座楚墓[2]。当时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陶器,开始把春秋楚墓与战国楚墓区别开来,将鬲、盂、罐组合的墓定为春秋时期,将鼎、敦、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时期,将鼎、盒、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晚期或西汉初年。这是最早对楚墓的分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楚墓的分期多参照此标准。
1964年至1965年期间,在江陵张家山、拍马山发掘了120余座楚墓[3],发现陶器组合有鬲、盂、长颈壶;鼎、簠、壶;鼎、敦、壶。认为鼎、簠、壶组合形式要早于鼎、敦、壶组合,于是便将鬲、盂、长颈壶组合定为春秋晚期,鼎、簠、壶组合定为战国早期,鼎、敦、壶组合定为战国中期,鼎、盒、壶组合定为战国晚期。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发现,楚墓中的鬲、盂、罐组合可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鼎、簠、壶组合与鼎、敦、壶组合在整个战国时期并行。
1957、1958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了两座大型楚墓,棺椁保存较好,出土一批铜器、漆器、陶器等,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楚国考古重大发现[4]。一号墓所出编钟铭文有“隹 屈
屈 晋人,救戎于楚競(境)”一语,郭沫若认为是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晋灭陆浑戎时事,定此墓为春秋末年[5]。顾铁符将长台关墓同长沙和寿县楚墓比较,看到既有长沙楚器风格,又与寿县楚器有相似之处,推断为战国时代楚墓[6]。1979年,顾铁符再次撰文考证信阳1号墓的墓主身份,认为墓主就是出土编钟铭文里的
晋人,救戎于楚競(境)”一语,郭沫若认为是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晋灭陆浑戎时事,定此墓为春秋末年[5]。顾铁符将长台关墓同长沙和寿县楚墓比较,看到既有长沙楚器风格,又与寿县楚器有相似之处,推断为战国时代楚墓[6]。1979年,顾铁符再次撰文考证信阳1号墓的墓主身份,认为墓主就是出土编钟铭文里的 ,是《左传》中所说的楚国左司马眅,这座墓的年代可能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7]。1986年出版的《信阳楚墓》报告,将此二墓定为战国早期。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关于此墓的年代一直不很明确。
,是《左传》中所说的楚国左司马眅,这座墓的年代可能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7]。1986年出版的《信阳楚墓》报告,将此二墓定为战国早期。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关于此墓的年代一直不很明确。
1965年底至1966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发掘了望山1、2号墓等几座中型楚墓,由于望山1号墓出土了越王勾践剑,勾践是春秋末年人,故多认为是战国初期的墓[8]。
总的看来,此阶段对楚文化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还比较模糊。
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楚考古发现与研究
对于楚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基本建立起来。1975年至1976年,在江陵纪南城东部雨台山发掘了500余座楚墓,分为七期,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之际[9]。1975年至1979年,在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近300座楚墓,也分为七期,从两周之际到战国晚期[10]。有了这两批墓葬材料,楚国东周陶器墓的分期基本搞清楚,并解决了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如鬲、盂、罐组合可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鼎、簠、壶组合与鼎、敦、壶组合在整个战国时期并存,这对此前楚墓分期的认识有了一个大的改观。
1979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为战国时期楚国铜器墓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11]。此墓虽不是楚墓,但所出大量的青铜器则具有浓厚的楚式器风格。墓中出土大型编钟中的一件镈钟铭文为:“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此是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为曾侯乙做的镈钟,曾侯乙墓的年代就可定在此年前后,属于战国早期。与曾侯乙铜器群相比,江陵望山1、2号墓、信阳长台关1号墓铜器群都要晚于曾侯乙墓,但又与战国晚期的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铜器群有一定的差距。此时期,学者对望山一号墓所出竹简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简文记录了墓主邵固祭祀的先王有“柬大王”“圣王” “邵王”(即楚简王、声王和悼王),祭祀的先君有“东宅公” “王孙喿”。墓主邵固以悼为氏,应为悼王之后,其间如果再隔其先君两代,邵固当死于威王或怀王之时,此墓属战国中期[12]。1978年,在江陵又发现了天星观1号墓,所出竹简记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纪郢之岁”一语,公孙鞅即商鞅,公元前361年入秦,卒于公元前338年,该墓的年代无疑就在这一时期,正好也是在楚宣王或威王之时[13]。1986年在湖北荆门包山墓地发掘的一座中型贵族墓,墓主是楚国左尹邵佗。墓中所出遣策有关于下葬年代的明确记载:“大司马邵骮(即悼滑)救郙之岁,亯月丁亥之日,左尹(葬)”,据研究,下葬的年代应为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也属战国中期楚怀王之时[14]。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将江陵这几座中型墓及信阳长台关墓的年代确定为战国中期,从而将战国楚铜器墓的编年搞清楚。
春秋楚墓年代学的建立较晚一些。1979年开始对当阳赵家湖近三百座东周楚墓进行整理,将属于春秋时期的十座小型铜器墓分为三期:第一期的铜器与春秋早期的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铜器近似[15],也相似于汉淮之间诸国的春秋早期铜器;第二期则与春秋中期的新郑李家楼郑伯墓铜器群相似[16];第三期又与春秋晚期的寿县蔡侯墓铜器群相似[17]。此外,襄阳山湾有七座春秋时期的铜器墓,也可看出存在着同样的演化规律[18]。1978年至1980年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发现,又使得刚刚认识到的春秋楚器的演化规律得到进一步证实[19]。在淅川下寺发掘了25座春秋楚墓,分为三期:早期的还保持着不少中原周文化风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中期的鼎、簋、壶等铜器则与新郑李家楼郑伯墓的同类器如出一范;晚期的鼎、敦等器又与寿县蔡侯墓同类器极其相似。属于中期的1、2、3号墓所出铜器中,多有“楚叔之孙倗”作器之铭,2号墓又出了王子午(楚令尹子庚)升鼎7件,上面也刻“倗”的铭文。学者认为,“倗”即“冯”,是卒于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继王子午为楚令尹的薳子冯[20]。此墓出的7件王子午升鼎毫无疑问是王子午之器,根据其加刻“倗”之铭文以及1、3号墓也有“楚叔之孙倗”作器的情况看,此组墓应是薳子冯的家室墓,2号墓主是薳子冯,时代应属春秋中期晚段。下寺早期的M7、M8比M1、M2、M3略早,应属春秋中期早段。下寺晚期M10、M11所出器物风格既然与寿县蔡昭侯墓的相似,属于典型的春秋晚期墓。
有了上述时代连续、年代确定的铜器群,加上郑器、蔡器、曾器这些受楚文化影响而可纳入楚文化系统的铜器群,楚国东周时期铜器墓年代学基本建立。
此时期除了重点对楚墓年代学进行研究外,还对江陵纪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与发掘。1975年,通过对纪南城大规模的勘查与发掘,初步确定纪南城现存城垣兴建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时[21]。那么,楚国更早的都城丹阳在何处?这就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1979年4月,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决定第二次年会在湖北举行,重点讨论楚文化。为第二次年会的召开作准备,俞伟超先生于1979年6月带队对江汉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作了《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报告:一、为什么要重视楚文化研究;二、楚文化发展的简单历程;三、考古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概况;四、楚文化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22]。为楚文化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为了寻找早期的楚都丹阳,俞伟超先生决定对当阳季家湖古城址进行发掘。1979年下半年,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部分师生参加,对当阳季家湖古城进行了试掘[23]。这次试掘,发现了古城的南墙和城壕,在城内一号台基处发现了大型房屋基址和散水,在杨家山子西部发现了制陶作坊遗迹等。判断季家湖古城的时代要比纪南城略早。1973年曾在一号台基出土一件甬钟,钲部铭文为“秦王卑命”,左鼓部八字“競坪王之定救秦戎”,该钟应是一套编钟中的一件。对于此城址的性质,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见解,或认为是楚丹阳故址[24],或认为是春秋时期的郢都[25],或认为属于春秋中晚期的郢都[26]。虽然此城的性质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基本确定是一座略早于纪南城的春秋时期楚城。
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也是倍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楚城。1961年、1963年曾对楚皇城遗址作过考古调查,认为上限可到战国,下限应在两汉[27]。1976年,再次进行了勘查和试掘,勘察简报判断此城址的年代,上溯至春秋战国,下续到秦汉以至更晚。推测此城春秋时可能是鄢的都邑,后成为楚的鄢郢[28]。也有学者认为楚皇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郢都[29]。由于对楚皇城的年代及性质一直存在歧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年再次对北城墙进行了发掘,确认城墙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下限一直延续到汉代。并对楚皇城是春秋时期楚郢都的观点提出商榷[30]。可以看出,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年代及性质还需继续探讨。
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楚考古发现与研究
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会议以楚文化问题作为研讨的重点[31]。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理事长夏鼐先生和副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就楚文化的研究和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夏鼐先生主要讲述了为什么要重视楚文化的研究、什么是楚文化、怎样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楚文化等[32]。苏秉琦先生则从楚文化探索的对象和目的、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和渊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文化面貌的阶段性和诸地区间文化关系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讲述。指出,“探索楚文化的中心目的——把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奥秘,把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真正揭示出来。” [33]
1981年6月,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于长沙召开了成立大会,首任理事长俞伟超先生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的学术报告,阐述了楚文化的概念问题,认为,“所谓楚文化,就是指最初是由楚人在楚国境内创造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有不同于其它文化的自身特征,当然这种特征是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变化,而基本具有这种特征的文化遗存,都可看作属于楚文化的范畴。”指出,根据楚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总过程,可分四个阶段重点探索楚文化。第一阶段,探索楚文化的渊源。把楚人建国之初的文化面貌搞清楚,进一步在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探讨其渊源。第二阶段,探索青铜时代的楚文化。这一阶段,楚文化的中心是在其都城丹阳一带,探清丹阳的地望,对研究楚人的青铜文化来说,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第三阶段,探索铁器时代的楚文化。重点研究春秋时期的郢都地望、楚文化的分区、楚墓的分类、分期和埋葬制度等问题[3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楚文化研究,正是按照夏鼐、苏秉琦、俞伟超三位先生所指引的方向进行的。
关于楚文化渊源研究。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之后,探索楚文化渊源的考古工作重点首先在江汉平原西部进行。在俞伟超先生的指导下,对沮漳河中游的当阳、远安两县进行了考古调查[35],对当阳磨盘山遗址[36]、冯山遗址、杨木岗遗址[37]、宜都石板巷子遗址[38]、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进行了发掘[39]。这些发掘均是为寻找楚文化的渊源进行的,但在这一区域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殷商时期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多处,唯独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遗址。俞伟超先生在分析了江汉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和殷商时期遗存后认为,楚文化是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原始文化基础上发展来的,在夏商周时期又进一步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真正的楚文化是到商周之际才形成的,在此以前诸阶段的前身文化,哪怕是最重要的来源,只能说是其渊源之一。” [40]1983年,俞伟超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江汉平原殷墟时期遗存之后至真正的楚文化还存在缺环,“探索楚文化的渊源,就是要研究周初以后的典型的楚文化遗存,究竟是由土著文化发展出来,还是从外地迁移而来,或者是综合了多种文化才形成?……寻找这些缺环,尤其是找到相当于殷墟阶段的遗存同西周楚文化的联结点,就是当前探索楚文化渊源的关键。” [41]1994年俞先生再次指出,“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大约是有多种文化因某些历史的因缘或机遇而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综合而成的。如果仅作单一连续线的观察,有可能将永远找不到楚的源头。假如从这种思路出发来考虑,则最初的楚文化,便可能包括本地的土著文化、早周文化等文化因素。……楚文化的源头实际是更加复杂的,具有如此众多源头的楚文化,如果和本地原有的文化相比,恐将面貌一新,堪称为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 [42] 俞先生着重提出要按着考古学文化系统、文化因素来寻找楚文化的多种源头。
关于楚都丹阳地望研究。《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关于丹阳的地望,传统文献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在南郡枝江”。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提出在今湖北秭归县。三、清宋翔凤《过庭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云:“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淅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淅。鬻熊所封正在于此。”学者对楚都丹阳地望进行了诸多研究,已由原来的诸多说法逐渐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湖北的沮漳河流域和河南的丹江流域。
关于楚纪南城的年代及性质问题。1975年对江陵纪南城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于1982年将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发表,初步确定纪南城现存城垣兴建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时,证实纪南城是楚郢都。资料发表之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多数学者认同纪南城是战国时期的郢都。但也出现了诸多不同见解。如有学者认为纪南城是楚的陪都,楚郢都应在湖北宜城境[43]。另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的郢都在宜城,楚昭王时迁至纪南城[44]。很长时期对纪南城的年代和性质还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关于楚墓分区、分类、分期研究。郭德维先生在《楚系墓葬研究》一书中[45],对楚墓的分区进行了研究,根据各区域楚墓特点主要分为12个区,梳理了各区域楚墓特点。对楚墓的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根据楚墓的规模、棺椁层数、椁内分室及随葬品组合等,将楚墓分为楚王墓、封君或上大夫墓、下大夫墓、士墓、庶民墓五个等级。并对楚墓的分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关于楚丧葬习俗研究。彭浩先生对楚墓随葬器物组合、葬具、墓葬等级进行了研究,指出楚墓的随葬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楚墓的鼎制有其自身特点,楚墓葬具的种类与《礼记》的有关记载大体是一致的[46]。1982年,在江陵马山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战国中期楚墓,葬具为单椁单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三部分,棺盖上有丝织物棺罩,棺罩上有一幅用一根竹枝条穿着的帛画。墓主仰身直肢葬,手脚用锦带捆缚,双手有绢制的“握” [47]。彭浩先生结合文献记载的丧葬礼制,对此墓所用的铭旌、帷荒、棺束、绞衾、掩、瑱、幎目、设握、屦綦结跗等楚国葬俗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楚国葬俗与文献记载之异同[48]。1986年,湖北荆门发掘了包山2号墓,胡雅丽对此墓的棺椁制度、下葬程序、葬具名称、棺之名实及棺饰等进行了考定,对楚国的葬制和葬俗作了较详细的研究[49]。
关于楚系礼器研究。刘彬徽先生全面收集了楚国青铜器资料,详细地进行了器物组合及形制方面的分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楚系青铜器发展系列,揭示出楚系青铜器的特征及发展脉络,并将楚系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同类器进行了对比,揭示出楚国青铜器的独特性,从而提出了“楚系”青铜器这一概念。该书备有详细的资料索引,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50]。
关于楚国与邻近地区文化关系的研究。高志喜先生著《楚文化的南渐》[51],阐述了楚文化向江南的发展。根据湖南所发现的楚墓,认为春秋早中期,楚文化已进入到湘水下游地区,春秋晚期进入到湘中地区,春秋末或战国初进入湘南地区。论述了江南地区楚墓的区域特征、丧葬礼俗及南楚文化与中原、巴、蜀、濮、越文化的关系。刘和惠先生著《楚文化的东渐》[52],梳理了淮河流域蔡国、群舒、徐国、吴国、越国的考古发现及文化特征,阐述了楚文化东进的历程及此地域战国晚期楚墓的特征。
楚文化的综合研究。杨权喜先生著《楚文化》一书[53],对楚文化的概念、楚文化的渊源、楚国的城址、墓葬、遗物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在楚文化渊源方面,全面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代至东周时期的考古发现,认为无论是考古学文化的发现,还是古文献记载,都可以证明荆山南麓至长江沿岸的鄂西地区,是西周时期楚系诸国或早期楚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这个区域便是典型楚文化的策源地。楚丹阳在包括枝江在内的沮漳河之西一带的可能性最大。对纪南城的形制、遗址、遗物及周边墓葬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纪南城是楚国的郢都所在地,始建于春秋末或战国初年,废弃年代为秦将白起拔郢之时,即公元前278年。怀疑春秋时期楚国之郢都并不在纪南城。对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淮阳陈城、寿县寿春城等城址布局、时代进行了研究。对楚墓进行了分区研究,分为11个区,对各区墓葬形制、棺椁制度、埋葬礼俗及随葬品特点等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对楚国的青铜器、铁器、漆木器、丝麻织物、竹简、陶器、玉石器等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楚文化》一书是进入新世纪之前对楚文化研究状况的全面梳理和总结。
1995年至1996年间,由张正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楚学文库》,对楚文化进行了各方面研究。丛书除上引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高志喜《楚文化的南渐》、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著作之外,还有张正明《楚史》、涂又光《楚国哲学史》、刘玉堂《楚国经济史》、蔡靖泉《楚文学史》、赵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皮道坚《楚艺术史》、杨匡民、李幼平《荆楚歌乐舞》、高价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赵德磬《楚国的货币》、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后德俊《楚国的矿业髹漆和玻璃制造》、滕任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此《楚学文库》集结楚学专著18部,多用楚国考古资料论述,足使读者获睹楚国历史文化发展之全豹。
四、进入二十一世纪楚考古发现与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界依然注重于楚文化渊源的研究,继续探寻西周时期的楚文化。考古工作的重点在三个区域:一是丹江至汉水一带,二是湖北荆山东麓蛮河流域,三是湖北沮漳河流域。
丹江至汉水一带楚文化渊源考古探索。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西周时期的商南县过风楼遗址,出土陶器主要有鬲、甗、罐、瓮等,时代为商末至西周中晚期,张天恩称之为“过风楼类型” [54]。这类遗存在丹江流域还发现有淅川下王岗遗址[55]、双河镇遗址等[56]。在鄂西北的汉水流域发现有十堰市大东湾遗址[57]、郧县辽瓦店子遗址[58]、大寺遗址[59]、均县朱家台遗址[60]、丹江口市观音坪遗址等[61]。尤其是郧县大寺遗址文化遗存比较丰富,地层关系清楚,分为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两期。简报认为,这类遗存从分布范围来看,“陕豫鄂交界地带的西周早、中期遗存,包括商南过凤楼、淅川下王冈、郧县大寺、辽瓦店子、十堰大东湾、丹江口观音坪、房县孙家坪等,均含有相同的一套以锥足鬲、扁柱足鬲、圆柱足鬲、甗、瓮、高领罐、盆、豆、杯等为主要器类的组合,其文化性质应相同,可视为同一文化类型。”指出这一文化类型与明确的春秋早期的楚文化“存在着较强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何晓琳综合论证了“过风楼类型”文化的特征及与春秋时期楚文化的关系,认为“过风楼类型文化与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它在商代末年到西周早期崛起于狭小的陕鄂交界山地,西周中晚期时向东南扩展,占据了整个丹江库区西侧的三省交汇地带,通过不断地吸收和整合周文化,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至春秋早期,进一步发展到襄宜平原和沮漳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东周时期独树一帜的楚文化。” [62]
湖北荆山东麓蛮河流域楚文化渊源考古探索。为了寻找早期的楚文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荆山东麓的蛮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楚文化遗址13处,复查大型遗址10余处。其中较重要的遗址有杨家台遗址、廖家河遗址、站家湾遗址、大堰遗址等,杨家台遗址、廖家河遗址、站家湾遗址属蛮河中下游宜城境内,分布于楚皇城之西地域,大堰遗址位于蛮河上游的南漳县境内。调查者根据所采集的陶器残片判断,杨家台遗址、廖家河遗址、站家湾遗址属于春秋时期的遗址,大堰遗址判定为西周时期,“为早期楚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 [63]。
湖北沮漳河流域楚文化渊源考古探索。2012年,宜昌万福垴遗址一窖穴出土甬钟12件,铜鼎1件,其中一件甬钟钲部刻有“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铭文[64]。关于这组甬钟的年代,有认为属西周晚期者[65],也有认为属西周早中期者[66],黄文新、赵芳超认为楚季钟铭文篆刻时间为西周中期晚段至西周晚期早段[67]。由于这是首次在这一地域发现的楚国重器,遂引起学界的重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此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初步判定此遗址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三个时期[68]。方勤根据沮漳河流域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从6个方面论证楚文化应源于沮漳河流域,沮漳河流域是西周早期楚被封为诸侯国的地望所在[69]。这是对楚源于沮漳河流域较全面地论述。
关于楚丹阳的继续探索。2010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70],其中《楚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楚先祖季连直到悼王、肃王时的居地都邑,再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对楚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对简文中的一些地名的释读仍有歧异。如传统文献所记楚熊绎“居丹阳”,而《楚居》则云“徙夷屯”,并且明确说自熊绎一直到熊渠“尽居夷屯”。“夷屯”究竟是指何处,则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见解。
《史记·楚世家》记:“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然《楚居》中没有记载丹阳,而是说熊绎徙于夷屯:“至酓 (繹)與屈
(繹)與屈 (紃),思(使)若(
(紃),思(使)若( )(嗌)
)(嗌) 卜
卜 (徙)於
(徙)於 (夷)
(夷) (屯),爲
(屯),爲 (楩—便)室=(室,室)既成,無以內之,乃
(楩—便)室=(室,室)既成,無以內之,乃 (竊)
(竊) (
( )人之
)人之 (犝)以祭。”整理者认为,“夷屯”即史书中的丹阳,近于鄀。学界对于夷屯的位置,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夷屯在汉水之南的荆山一带[71]。第二种意见认为夷屯应靠近楚的夷陵,夷陵是楚的先王陵,位于宜昌,临近沮漳河流域,或认为宜昌万福垴遗址,也属于夷屯地域[72]。第三种意见认为夷屯应与鄀临近,鄀位于丹江支流淅水流域,夷屯应在丹江流域[73]。
(犝)以祭。”整理者认为,“夷屯”即史书中的丹阳,近于鄀。学界对于夷屯的位置,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夷屯在汉水之南的荆山一带[71]。第二种意见认为夷屯应靠近楚的夷陵,夷陵是楚的先王陵,位于宜昌,临近沮漳河流域,或认为宜昌万福垴遗址,也属于夷屯地域[72]。第三种意见认为夷屯应与鄀临近,鄀位于丹江支流淅水流域,夷屯应在丹江流域[73]。
关于楚郢都的继续探索。传统的观点一直将楚郢都认定在江陵纪南城。清华简《楚居》则彻底推翻了传统观点,其中记载,至楚武王自宵徙居免,“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之后历届楚王迁居十几处郢。尤其是武王、文王时期,就徙居有疆郢、湫郢、樊郢、为郢、免郢,至庄敖由免郢福丘迁居鄀郢。这些“郢”的具体地点虽还有诸多不同见解,但研究者基本都将其推定在宜城平原及附近区域内。春秋时期的诸“郢”在宜城平原,也可用考古资料来印证。目前在宜城平原一带已发现多处春秋时期的楚文化的遗址,有些遗址面积比较大,堆积比较厚,内涵比较丰富,从所处地理位置及地貌形势来看,其中的一些大遗址有可能就是楚武王、文王时期所居的诸“郢”。如宜城楚皇城以西12公里处的郭家岗遗址[74],遗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处于四周低洼的高台地上。在郭家岗遗址西北数公里的朱市曾发现“蔡大膳夫”簠和鼎青铜器[75],在朱市西约4公里的南漳与宜城交界的安乐堰还出土“蔡侯朱之缶”青铜器[76]。徐少华先生指出,“蔡哀侯、蔡侯朱均先后客死于楚,他们的居地当在楚郢都或其附近不远。” [77]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在安乐堰东侧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春秋时期杨家台遗址[78],遗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处于高台地上,四周由环濠环绕,环濠南侧、东侧发现有进入遗址的阶梯状遗迹,环濠与遗址南侧、东侧的古河道相通。从杨家台、郭家岗等大遗址所处时代、地理位置、地貌形势以及附近出土蔡侯王室重器来看,这些大遗址有可能就是楚武王、文王时期所居的诸“郢”所在。
关于纪南城始建年代及性质再探讨。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南垣东部的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进行了发掘[79]。2011~2012年,又对纪南城内松柏区30号台基西南部进行了发掘[80]。通过这两次发掘,对1975年所推断的纪南城始建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进行了修正,认为纪南城城墙的建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甚至可能晚到战国中期晚段,城内主要宫殿基址定为战国中期。这是通过新的考古资料对纪南城的新认知。
纪南城究竟是哪个“郢”?也出现了诸多不同见解。早前,黄锡全先生根据纪南城周边楚墓出土竹简中多记有“戚郢”,认为是指战国时期的纪南城遗址(纪郢)[81]。清华简《楚居》发表后,刘彬徽认为《楚居》记楚文王“始都为郢”是正确的,“为郢”“应在今荆山南麓至沮漳河流域,也可能仍在今荆州区内[82]。也有学者认为,楚武王所居的“疆郢”就是纪南城,“楚国此都之旧名或作‘疆郢’,或称‘南郢’,其作‘纪郢’者则颇有可能是由‘纪南城’衍生出出来的名称。” [83]守彬则认为,《楚居》中所记“×郢”并非城邑名,“凡称‘×郢’者皆是宫殿名称”,“楚国自武王以来,都城整体名为‘郢’,而楚王自身常住之宫,名为‘×郢’。”并认为,“春秋时楚都‘郢’在季家湖,战国时(秦白起拔郢前)在纪南城。” [84]由此看来,有关楚纪南城的年代及性质还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关于楚王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是一座屡经盗掘的墓葬,墓葬形制及墓地布局已不清楚。1981年至198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南淮阳马鞍冢进行了发掘,推测为楚顷襄王夫妇墓[85]。马鞍冢为南北两冢并列,南冢设有东西两条墓道,呈“中”字形;北冢只设东墓道,呈“甲”字形。两墓被历代盗扰严重。两墓西侧有各自相对应的车马陪葬坑,南车马坑葬泥马20余匹,车23辆,旌旗6面。北车马坑葬马24匹,车8辆。这是对楚王陵葬制的初步认识。
对于大型楚王陵墓的调查与研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江陵纪南城西北分布有数处大型陵墓。2006年至2008年,荆州博物馆对纪南城西北约26公里处的熊家冢墓地进行了发掘[86]。墓地中两座大型墓冢南北排列,南为主冢,北为祔冢,经勘查,两墓均设有东墓道,墓坑呈“甲”字形。在两墓冢西侧发现排列有序的车马坑共40座,其中大车马坑靠近两冢,南北长132.6米,东西宽11~12米,坑内车辆分两排放置,排列有序。在主冢的南侧发现4列24排计92座殉葬墓,已发掘南殉葬墓54座,墓内殉人一般有单棺,也有一棺一椁者,棺内有少量玉饰器、铜兵器等随葬品。祔冢北侧发现35座殉葬墓,也排列整齐,基本也是呈4列排列。另外在主冢侧还发现许多祭祀坑。对于熊家冢陵墓的墓主,学界一般认为是楚王陵墓。蒋鲁敬对祔冢北侧一殉葬墓出土铜鼎、铜壶形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时代应属战国早期[87]。如依此推测,熊家冢有可能是楚惠王的陵墓。
2011年至2012年,荆州博物馆对纪南城西约7公里处的冯家冢墓地进行了勘探与发掘[88]。冯家冢墓地平面布局与熊家冢墓地相似,墓地中一大一小两墓冢南北排列。两冢西侧发现有2座大型车马坑。大冢南侧发现24座殉葬墓,小冢北侧发现94座殉葬墓,坑位排列有序、规模相当、方向一致、间距相当,与熊家冢墓地的殉葬墓布局极为相似,应为遵循同一葬制而设。推测冯家冢墓地为战国早期晚段至战国中期早段期间的一代楚王陵。
2011年,荆州博物馆对冯家冢墓地北约1.4公里的平头冢墓地进行了考古勘察[89]。墓地中部也是一大一小两墓冢南北排列,两墓冢西侧发现2座大型车马坑,还发现有50余座祭祀坑及陵园外围建筑的迹象。但该墓地没有发现殉葬墓的迹象。此似乎表明平头冢墓地比熊家冢墓地、冯家冢墓地的时代要晚一些。
通过对这几处被推测为楚王陵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大体了解了战国时期楚王陵的布局与建制。尤其是楚王陵殉葬墓的殉葬方式是东周各国殉葬墓中比较特殊的。东周时期各区域的殉葬情况有所不同,两周、虢、郑、卫、晋等中原地区各国,在东周时期已罕见殉葬实例,魏、赵在战国时期还有殉葬墓,但为数不多。姬姓的燕国、鲁国也少见东周时期的殉葬墓。但西部的秦,北部的北狄,东部的齐、莒,东南的徐、吴、越,南部的楚国等,还盛行殉葬风俗,只是流行的时间有差异。熊家冢、冯家冢殉葬墓的发现似乎表明楚国的殉葬风俗拖延得更晚一些[90]。
综观楚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从二十世纪初的初步认知,到目前全方位、多学科研究楚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都在不断深入,不断突破,不断取得新成果。现在,楚文化研究新一代的中坚力量已经形成,在前辈多年辛勤打造的基础上,一定会将这一研究继续深入发展,进一步揭示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高崇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4期)